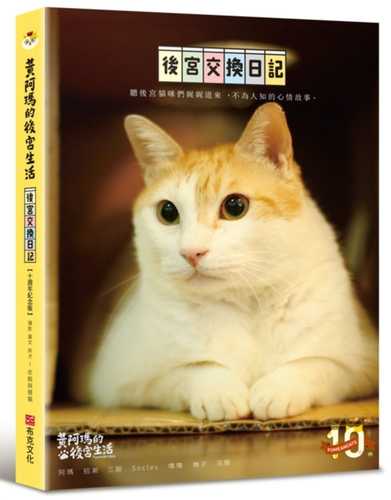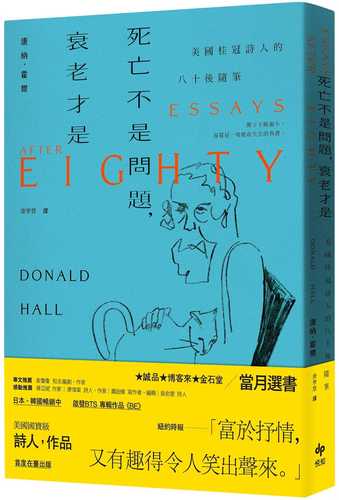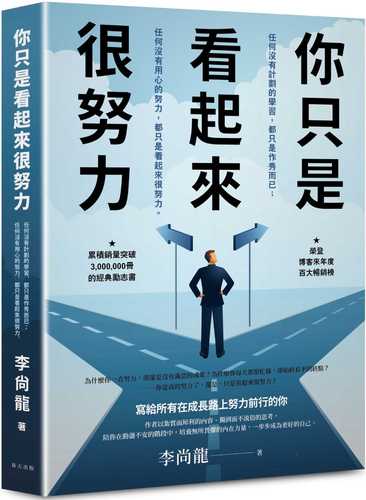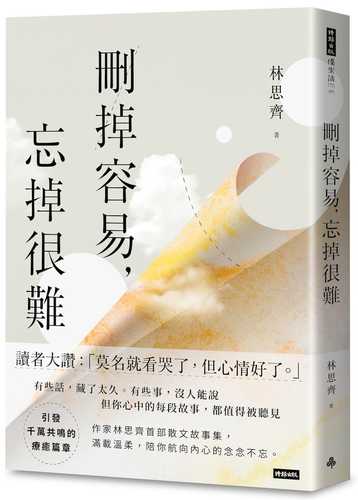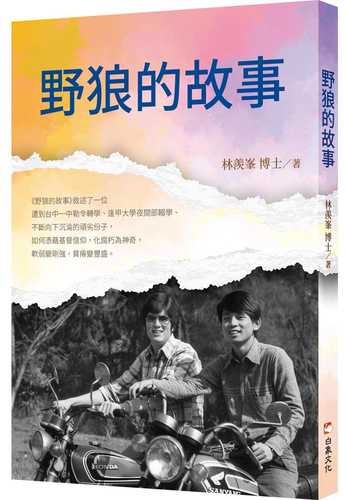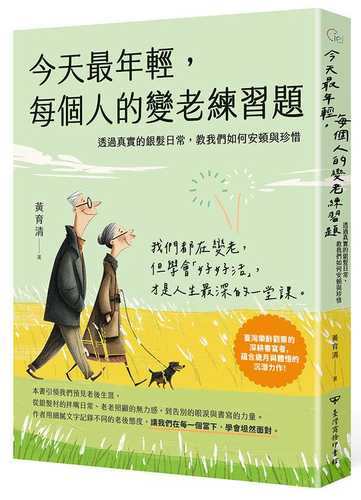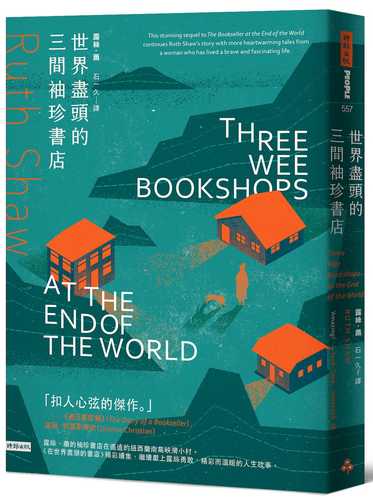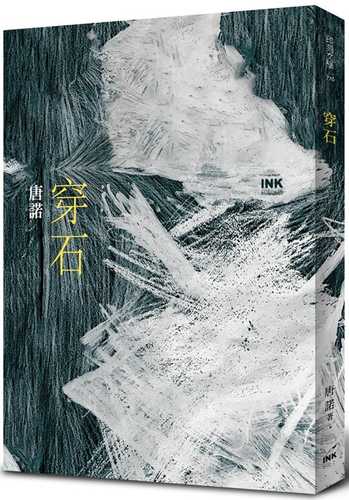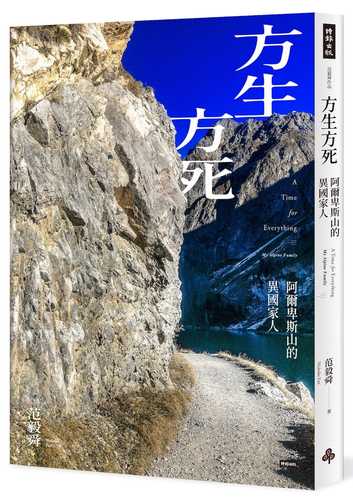2006年,我为肝癌晚期的朋友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、陪她走向生命的终点。
1个月后,在朋友的追悼会上,我遭受大家的谴责,却无力反驳,被淹没在各种攻击的声音里。
休学,躲在家里一年未与外界接触,也再没有说过话。
2007年,精神科的医生给了我一纸诊断: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。
我离世朋友曾在福利院生活过一年,却从不谈论在福利院的生活。
医生觉得,走进她的过去,走进一家福利院,也许能重新打开我的人生。
2008年,我成为福利院一个“张口无言”的志愿者,帮助保育员阿姨照顾孩子。
初来乍到,我不知道是否会拥抱谁,又是否会获得谁的拥抱。
1个月后,在朋友的追悼会上,我遭受大家的谴责,却无力反驳,被淹没在各种攻击的声音里。
休学,躲在家里一年未与外界接触,也再没有说过话。
2007年,精神科的医生给了我一纸诊断: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。
我离世朋友曾在福利院生活过一年,却从不谈论在福利院的生活。
医生觉得,走进她的过去,走进一家福利院,也许能重新打开我的人生。
2008年,我成为福利院一个“张口无言”的志愿者,帮助保育员阿姨照顾孩子。
初来乍到,我不知道是否会拥抱谁,又是否会获得谁的拥抱。


 放入
放入